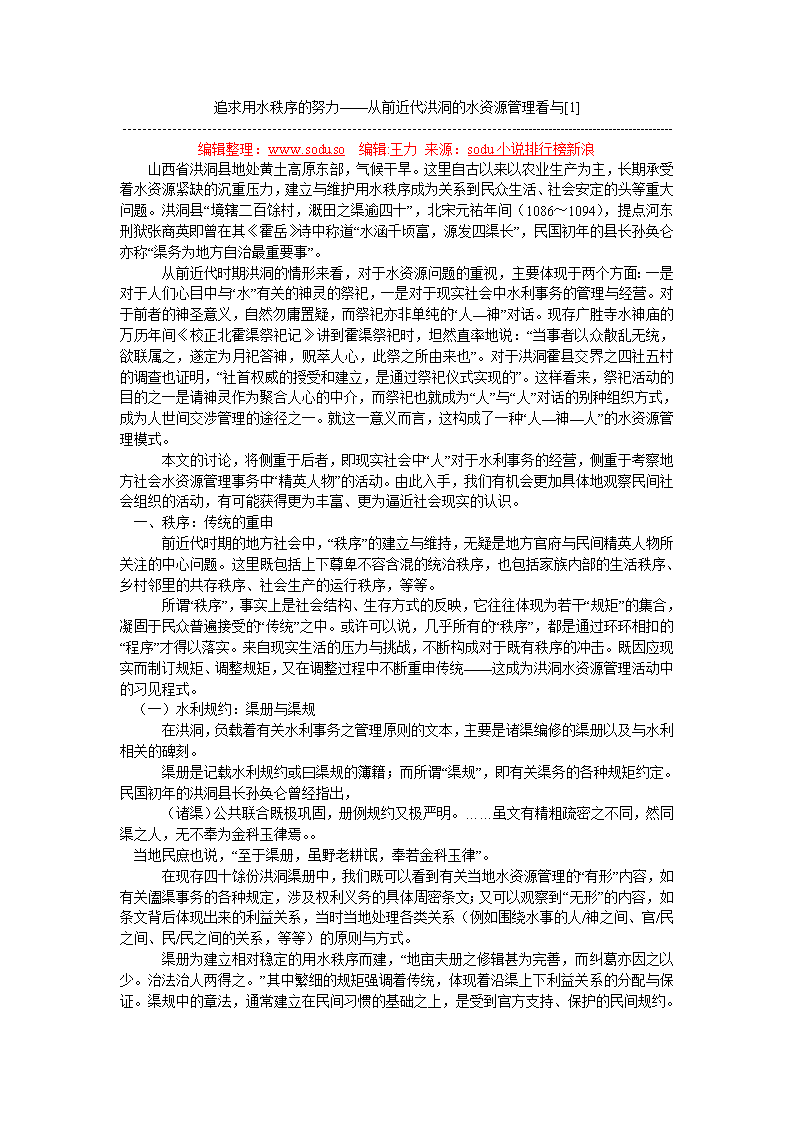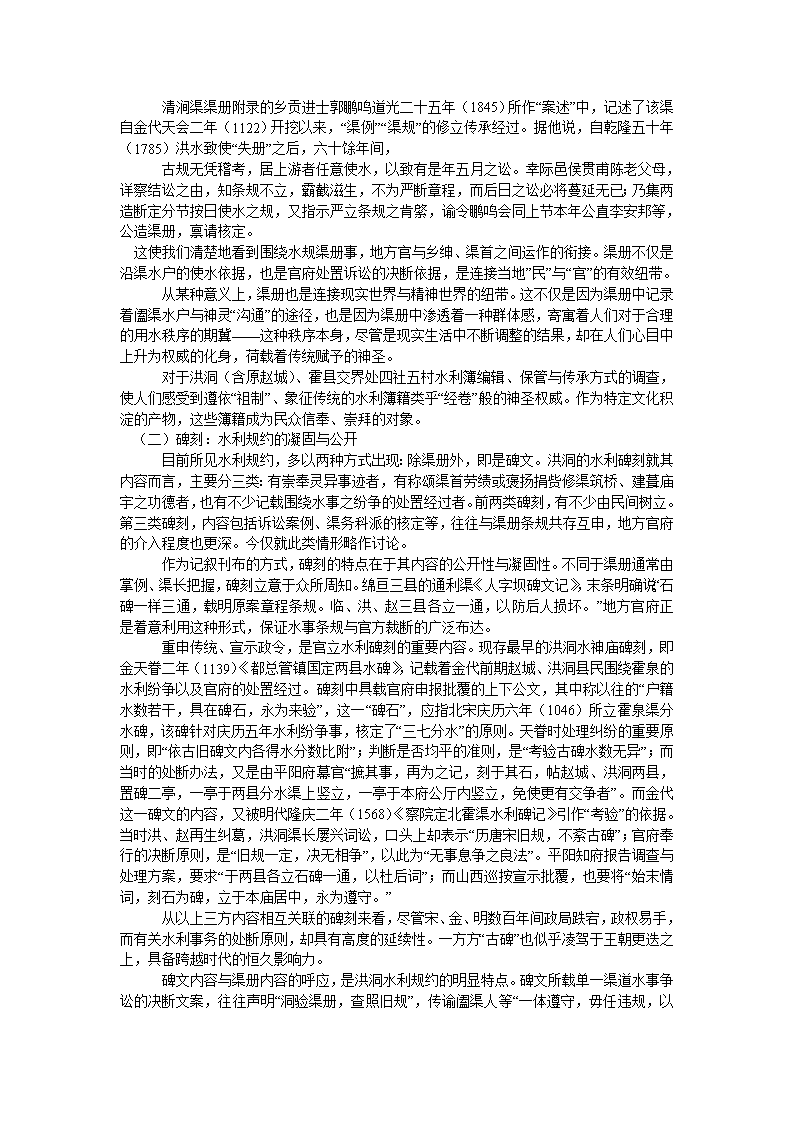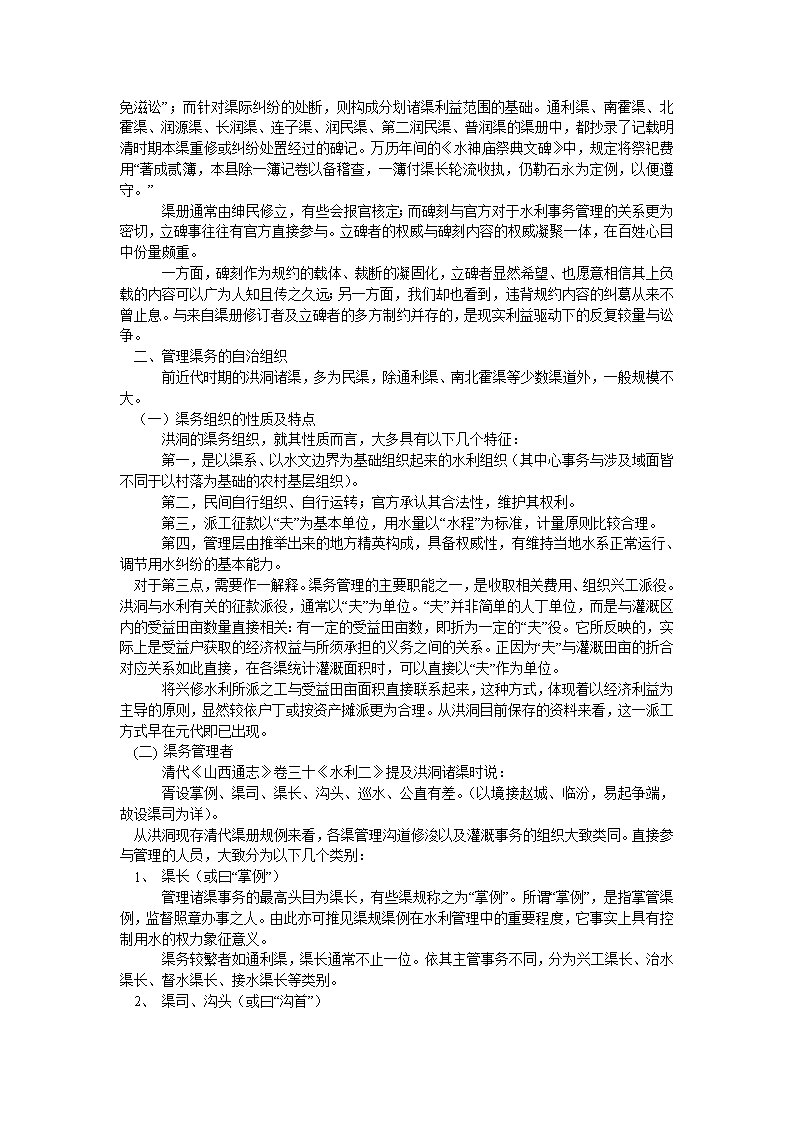- 38.50 KB
- 5页
- 1、本文档共5页,可阅读全部内容。
- 2、本文档由网友投稿或网络整理,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处理。
'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——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与[1]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编辑整理:www.sodu.so编辑:王力来源:sodu小说排行榜新浪 山西省洪洞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,气候干旱。这里自古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,长期承受着水资源紧缺的沉重压力,建立与维护用水秩序成为关系到民众生活、社会安定的头等重大问题。洪洞县“境辖二百馀村,溉田之渠逾四十”,北宋元祐年间(1086~1094),提点河东刑狱张商英即曾在其《霍岳》诗中称道“水涵千顷富,源发四渠长”,民国初年的县长孙奂仑亦称“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”。 从前近代时期洪洞的情形来看,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重视,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:一是对于人们心目中与“水”有关的神灵的祭祀,一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水利事务的管理与经营。对于前者的神圣意义,自然勿庸置疑,而祭祀亦非单纯的“人—神”对话。现存广胜寺水神庙的万历年间《校正北霍渠祭祀记》讲到霍渠祭祀时,坦然直率地说:“当事者以众散乱无统,欲联属之,遂定为月祀答神,贶萃人心,此祭之所由来也”。对于洪洞霍县交界之四社五村的调查也证明,“社首权威的授受和建立,是通过祭祀仪式实现的”。这样看来,祭祀活动的目的之一是请神灵作为聚合人心的中介,而祭祀也就成为“人”与“人”对话的别种组织方式,成为人世间交涉管理的途径之一。就这一意义而言,这构成了一种“人—神—人”的水资源管理模式。 本文的讨论,将侧重于后者,即现实社会中“人”对于水利事务的经营,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“精英人物”的活动。由此入手,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,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、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。
一、秩序:传统的重申 前近代时期的地方社会中,“秩序”的建立与维持,无疑是地方官府与民间精英人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。这里既包括上下尊卑不容含混的统治秩序,也包括家族内部的生活秩序、乡村邻里的共存秩序、社会生产的运行秩序,等等。 所谓“秩序”,事实上是社会结构、生存方式的反映,它往往体现为若干“规矩”的集合,凝固于民众普遍接受的“传统”之中。或许可以说,几乎所有的“秩序”,都是通过环环相扣的“程序”才得以落实。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挑战,不断构成对于既有秩序的冲击。既因应现实而制订规矩、调整规矩,又在调整过程中不断重申传统——这成为洪洞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习见程式。(一)水利规约:渠册与渠规 在洪洞,负载着有关水利事务之管理原则的文本,主要是诸渠编修的渠册以及与水利相关的碑刻。 渠册是记载水利规约或曰渠规的簿籍;而所谓“渠规”,即有关渠务的各种规矩约定。民国初年的洪洞县长孙奂仑曾经指出, (诸渠)公共联合既极巩固,册例规约又极严明。……虽文有精粗疏密之不同,然同渠之人,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焉。。当地民庶也说,“至于渠册,虽野老耕氓,奉若金科玉律”。 在现存四十馀份洪洞渠册中,我们既可以看到有关当地水资源管理的“有形”内容,如有关阖渠事务的各种规定,涉及权利义务的具体周密条文;又可以观察到“无形”的内容,如条文背后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,当时当地处理各类关系(例如围绕水事的人/神之间、官/民之间、民/民之间的关系,等等)的原则与方式。 渠册为建立相对稳定的用水秩序而建,“地亩夫册之修辑甚为完善,而纠葛亦因之以少。治法治人两得之。”其中繁细的规矩强调着传统,体现着沿渠上下利益关系的分配与保证。渠规中的章法,通常建立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之上,是受到官方支持、保护的民间规约。 清涧渠渠册附录的乡贡进士郭鹏鸣道光二十五年(1845)所作“案述”中,记述了该渠自金代天会二年(1122)开挖以来,“渠例”“渠规”的修立传承经过。据他说,自乾隆五十年(1785)洪水致使“失册”之后,六十馀年间, 古规无凭稽考,居上游者任意使水,以致有是年五月之讼。幸际邑侯贯甫陈老父母,详察结讼之由,知条规不立,霸截滋生,不为严断章程,而后日之讼必将蔓延无已;乃集两造断定分节按日使水之规,又指示严立条规之肯綮,谕令鹏鸣会同上节本年公直李安邦等,公造渠册,禀请核定。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围绕水规渠册事,地方官与乡绅、渠首之间运作的衔接。渠册不仅是沿渠水户的使水依据,也是官府处置诉讼的决断依据,是连接当地”民”与“官”的有效纽带。 从某种意义上,渠册也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纽带。这不仅是因为渠册中记录着阖渠水户与神灵“沟通”的途径,也是因为渠册中渗透着一种群体感,寄寓着人们对于合理的用水秩序的期冀——这种秩序本身,尽管是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的结果,却在人们心目中上升为权威的化身,荷载着传统赋予的神圣。 对于洪洞(含原赵城)、霍县交界处四社五村水利簿编辑、保管与传承方式的调查,使人们感受到遵依“祖制”、象征传统的水利簿籍类乎“经卷”般的神圣权威。作为特定文化积淀的产物,这些簿籍成为民众信奉、崇拜的对象。
(二)碑刻:水利规约的凝固与公开 目前所见水利规约,多以两种方式出现:除渠册外,即是碑文。洪洞的水利碑刻就其内容而言,主要分三类:有崇奉灵异事迹者,有称颂渠首劳绩或褒扬捐赀修渠筑桥、建葺庙宇之功德者,也有不少记载围绕水事之纷争的处置经过者。前两类碑刻,有不少由民间树立。第三类碑刻,内容包括诉讼案例、渠务科派的核定等,往往与渠册条规共存互申,地方官府的介入程度也更深。今仅就此类情形略作讨论。 作为记叙刊布的方式,碑刻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公开性与凝固性。不同于渠册通常由掌例、渠长把握,碑刻立意于众所周知。绵亘三县的通利渠《人字坝碑文记》,末条明确说:“石碑一样三通,载明原案章程条规。临、洪、赵三县各立一通,以防后人损坏。”地方官府正是着意利用这种形式,保证水事条规与官方裁断的广泛布达。 重申传统、宣示政令,是官立水利碑刻的重要内容。现存最早的洪洞水神庙碑刻,即金天眷二年(1139)《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》,记载着金代前期赵城、洪洞县民围绕霍泉的水利纷争以及官府的处置经过。碑刻中具载官府申报批覆的上下公文,其中称以往的“户籍水数若干,具在碑石,永为来验”,这一“碑石”,应指北宋庆历六年(1046)所立霍泉渠分水碑,该碑针对庆历五年水利纷争事,核定了“三七分水”的原则。天眷时处理纠纷的重要原则,即“依古旧碑文内各得水分数比附”;判断是否均平的准则,是“考验古碑水数无异”;而当时的处断办法,又是由平阳府幕官“摭其事,再为之记,刻于其石,帖赵城、洪洞两县,置碑二亭,一亭于两县分水渠上竖立,一亭于本府公厅内竖立,免使更有交争者”。而金代这一碑文的内容,又被明代隆庆二年(1568)《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》引作“考验”的依据。当时洪、赵再生纠葛,洪洞渠长屡兴词讼,口头上却表示“历唐宋旧规,不紊古碑”;官府奉行的决断原则,是“旧规一定,决无相争”,以此为“无事息争之良法”。平阳知府报告调查与处理方案,要求“于两县各立石碑一通,以杜后词”;而山西巡按宣示批覆,也要将“始末情词,刻石为碑,立于本庙居中,永为遵守。” 从以上三方内容相互关联的碑刻来看,尽管宋、金、明数百年间政局跌宕,政权易手,而有关水利事务的处断原则,却具有高度的延续性。一方方“古碑”也似乎凌驾于王朝更迭之上,具备跨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。 碑文内容与渠册内容的呼应,是洪洞水利规约的明显特点。碑文所载单一渠道水事争讼的决断文案,往往声明“洞验渠册,查照旧规”,传谕阖渠人等“一体遵守,毋任违规,以免滋讼”;而针对渠际纠纷的处断,则构成分划诸渠利益范围的基础。通利渠、南霍渠、北霍渠、润源渠、长润渠、连子渠、润民渠、第二润民渠、普润渠的渠册中,都抄录了记载明清时期本渠重修或纠纷处置经过的碑记。万历年间的《水神庙祭典文碑》中,规定将祭祀费用“著成贰簿,本县除一簿记卷以备稽查,一簿付渠长轮流收执,仍勒石永为定例,以便遵守。” 渠册通常由绅民修立,有些会报官核定;而碑刻与官方对于水利事务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,立碑事往往有官方直接参与。立碑者的权威与碑刻内容的权威凝聚一体,在百姓心目中份量颇重。 一方面,碑刻作为规约的载体、裁断的凝固化,立碑者显然希望、也愿意相信其上负载的内容可以广为人知且传之久远;另一方面,我们却也看到,违背规约内容的纠葛从来不曾止息。与来自渠册修订者及立碑者的多方制约并存的,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反复较量与讼争。二、管理渠务的自治组织 前近代时期的洪洞诸渠,多为民渠,除通利渠、南北霍渠等少数渠道外,一般规模不大。(一)渠务组织的性质及特点 洪洞的渠务组织,就其性质而言,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: 第一,是以渠系、以水文边界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水利组织(其中心事务与涉及域面皆不同于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)。 第二,民间自行组织、自行运转;官方承认其合法性,维护其权利。 第三,派工征款以“夫”为基本单位,用水量以“水程”为标准,计量原则比较合理。 第四,管理层由推举出来的地方精英构成,具备权威性,有维持当地水系正常运行、调节用水纠纷的基本能力。对于第三点,需要作一解释。渠务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,是收取相关费用、组织兴工派役。洪洞与水利有关的征款派役,通常以“夫”为单位。“夫”并非简单的人丁单位,而是与灌溉区内的受益田亩数量直接相关:有一定的受益田亩数,即折为一定的“夫”役。它所反映的,实际上是受益户获取的经济权益与所须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关系。正因为“夫”与灌溉田亩的折合对应关系如此直接,在各渠统计灌溉面积时,可以直接以“夫”作为单位。 将兴修水利所派之工与受益田亩面积直接联系起来,这种方式,体现着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原则,显然较依户丁或按资产摊派更为合理。从洪洞目前保存的资料来看,这一派工方式早在元代即已出现。(二)渠务管理者 清代《山西通志》卷三十《水利二》提及洪洞诸渠时说: 胥设掌例、渠司、渠长、沟头、巡水、公直有差。(以境接赵城、临汾,易起争端,故设渠司为详)。从洪洞现存清代渠册规例来看,各渠管理沟道修浚以及灌溉事务的组织大致类同。直接参与管理的人员,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:1、渠长(或曰“掌例”) 管理诸渠事务的最高头目为渠长,有些渠规称之为“掌例”。所谓“掌例”,是指掌管渠例,监督照章办事之人。由此亦可推见渠规渠例在水利管理中的重要程度,它事实上具有控制用水的权力象征意义。 渠务较繁者如通利渠,渠长通常不止一位。依其主管事务不同,分为兴工渠长、治水渠长、督水渠长、接水渠长等类别。2、
渠司、沟头(或曰“沟首”) 在渠长指令下负责“浇灌、盗水等项”事务。3、巡水 按时插移水牌、巡视水行状况,并且负责巡视保护渠上石桥等建筑。4、夫头 平时受命收敛钱物、兴工时带领管理夫役。 除去直接管理用水事务的不同层次组织者之外,还有专门负责祭祀进香的香首、盘首(盘头)。在缺乏固定水源处,祭祀祈雨等类乞灵于“天”的活动意义尤其重要,香首、盘头的地位会更加凸显。(三)对于渠首的推选 渠首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产生,轮流担当。就北霍渠两通“历年渠长”题名碑来看,自明嘉靖后期到清乾隆年间,大体上说,“治水之长,一年一更”。而通利渠则允许“蝉联接充”。1、基本资格: 各渠具体规定不同,但多注重家道、人品、能力等。 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修成的《重修通利渠册》“选举”中规定: 选举渠长,务择文资算法粗能通晓,尤须家道殷实、人品端正、干练耐劳、素孚乡望者,方准合渠举充。所谓“家道殷实”,通常就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而言。据该渠乡绅孙恩瀛等说:“孙曲村历来村中递选渠长,必取……当年种地十亩之大户。”由此可知当地对于渠长资格之实际核定办法。 选择渠长的基本原则大体上集中于两个方面:一为“家道殷实”(“上户”、“地多”),一为本人能孚众望。也有的明确规定须自夫头或巡水中选充。这几项条件,实际上已将候选者框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。2、
推选方式: “公推”、“公举”,是诸渠渠册中常见的措辞。渠长偶有约定由一姓世代相传者,但通常要由沿渠诸村“公共推选”。推选方式包括逐届临时推举,符合资格条件者依次轮流,或是“签选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数情形下,并非由全体相关水户直接选举,而是在“合渠公举”的名义下,由渠道各受益村的一些“代表人物”聚议推举出来的。规模有限的水渠如均益、天润、广平等渠,由合渠“选保”“轮膺”;而规模较大、涉及数县的通利渠,则需先集议推举,继而在官方的监督下完成。 通利渠号称洪洞“第一渠”,绵亘赵城、洪洞、临汾三县二十一村,浇灌土地两万六千馀亩,涉及范围广、人户众多;其渠长的推举方式,经过酝酿调整,应该说是洪洞诸渠中最为完备的。与此相关的材料,集中在刻石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十二月的通利、式好、两济渠《人字坝碑文记》附录,修订于次年的《重修通利渠册序》以及《增定通利渠规十二则》中。 当时的平阳知府刘光炘查勘通利渠截河阻水案,传集该渠绅民孙恩瀛等,令其“会议一经久之计”。孙恩瀛等人的建议集中于选任渠长的方式上: 合渠上中下三节凡有渠长之村,例系九月初一日签换。……绅等拟仿上三村成法,于应充渠长之村预择公正勤谨、堪胜渠长之任者各若干家,著册定案,作为预备渠长,另单呈核,以便置签候掣。每年即在此若干家内掣签。恐人事变迁,富贵无常,合渠绅民每届十年会议一次,其有中落之家以及事故变迁,公议具呈免充;并各该村有新兴之家,公议更举续增。且续增免充,必合渠绅民认可,方得增减,如有不合宜之处,从长再议。据此,通利渠“签换”渠长已是往年惯例,此时则效法被称作“官渠”的上三村之施行方式,使其步骤更趋完善。首先是限定于某些“应充渠长之村”,按一定标准保举推选“预备渠长”,“合渠德望素隆之耆老、乡里矜式之缙绅公同认可”,才可以呈报官方核准列入预举册内;然后即在此范围内经官府“临时当堂掣签点充”,决定正式渠长人选。 拟议中的这一过程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:其一,“预择”预备渠长的标准:尽管提及“公正勤谨、堪胜渠长之任”,选择却是落实在“若干家”而非某些个人身上的,而且“富贵无常”、家道“中落”是导致预选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,取而代之者,则是“新兴之家”。由此可见,选择虽然会考虑多种因素,其关键却在于家业背景而不在于个人素质。其二,“签换渠长”的做法,与明清以来中央政府铨选任命官吏时的“掣签”“签派”办法一脉相承。在矛盾纷繁的背景下,这一方式靠确定“预择”标准来控制备选范围,保证由富裕民户出任渠长,同时通过带有偶然性的“掣签”,避免垄断、请托之弊,防范“富民避充、奸民争充”;而对于“置签”的审核及“掣签”的“当堂”完成,则使官方的权威性渗透入这一过程之中。'
您可能关注的文档
- 东莞市水资源管理系统
- 管理学其它毕业论文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及启示
- 管理学其它毕业论文 高校水资源管理初探
- 广东:全力扼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“三条红线”
- 千阳县水资源管理办法
- 工学水利工程毕业论文 浅析黄河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
- 工学水利工程毕业论文 论张掖市甘州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措施及对策
- 工学水利工程毕业论文 赴美国水资源管理培训报告
- 工学水利工程毕业论文 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监控指挥系统研制与推广
- 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
- 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使用指南
- 江苏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招标文件_技术部分__改_(3)_20010603
- 全省水资源管理工作会议
-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范文
- 辽源市水资源管理中心
- 从国外经验谈珠江水资源管理的对策与措施
- 【精品】乡镇关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
- 黑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中行政首长负责制探讨